(上)面對大規模捕殺·穿山甲走向滅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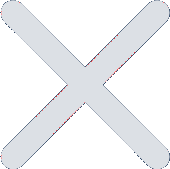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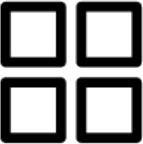

■部分圖片由艾麗莎潘姜提供
■報道/王麗萍
ADVERTISEMENT
穿山甲因為會挖洞和身體覆蓋堅硬的鱗片而得名,其個性膽小而敏感,一被驚嚇就會把身體捲縮成球型,原本能抵卸天敵的天性,遇上人類卻可輕被捉走,更成為國際走私、販運最多的哺乳類動物,在大規模捕殺下走向滅絕。
10年100萬隻遭捕殺
根據國際野生物貿易委員會(TRAFFIC),在過去10年,遭獵殺的穿山甲高達100萬隻,儘管在2017年,穿山甲在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CITES)下,被禁止進行國際間的貿易,但在該禁令後的短短几年,估計有50萬隻穿山甲被捕殺,可見在強烈與高價的市場需求下,盜殺活動依然猖獗。
沙巴野生動物局在2009年的一次突擊行動中,截獲一個穿山甲走私集團收購資料的記錄本,顯示在2007年至2009年之間,全州各地共有逾2萬隻穿山甲被盜獵提供予非法集團,反映州內穿山甲非法盜獵與走私的嚴重性。
2018年,沙巴把州內唯一的穿山甲品種,即馬來穿山甲(Sunda Pangolin)列為一級保護野生動物,禁止捕捉、獵殺或販賣,但近年來破獲的大宗穿山甲走私案仍有所聞,其中2017年在實邦加集裝箱碼頭截獲逾8000公斤、價值逾1億令吉的穿山甲鱗片走私案,以及2019年2月在擔波羅裡破獲穿山甲盜獵案,起獲市值3400萬令吉的穿山甲肉、鱗片及61隻活穿山甲。
這沙巴除了在跨國穿山甲走私活動中扮演來源國和轉運站的角色,近年來,隨著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暗地操作及提供穿山甲與其他野生動物料理予遊客的野味黑店,亦是執法當局頭痛的問題,極度瀕危的馬來穿山甲面對無休止的盜獵、販售而岌岌可危。

全球共8種穿山甲
全球共有8種穿山甲,分佈在亞洲及非洲。亞洲的穿山甲除了主要分佈在東南亞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柬埔寨、泰國等的馬來穿山甲(學名:Manis Javanica,又名爪哇穿山甲或爪哇鯪鯉),還有在印度的印度穿山甲( Indian pangolin)、在中國、香港和臺灣的中華穿山甲(Chinese pangolin),以及在菲律賓的菲律賓穿山甲( Philippine pangolin)。
非洲則有4種穿山甲,即黑腹樹穿山甲 (Black-bellied tree pangolin)、長尾穿山甲(Long-tailed pangolin)、巨地穿山甲( Giant pangolin)與南非地穿山甲( Temminck's ground pangolin)。
全部穿山甲都在迅速減少中,也都在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紅色名錄中列為易危至極危的物種,其中馬來穿山甲與中華穿山甲被列為極度瀕危,下一個階段就是野外滅絕。
穿山甲的全身上下,包括肉、鱗片和外皮都被用於商業用途,主要市場是中國和越南。所有穿山甲從走私來源國,尤其是非洲,先運到中轉站,最後運到中國和越南。在亞洲市場,一隻穿山甲可售達1000美元,全球黑市更可售達3000美元,以致穿山甲的需求不斷攀升,在人類趕盡殺絕下面對悲慘命運。

塔塔納族視為神聖動物
根據訪間式調查,杜順塔塔納族(Tatana)據說過去視穿山甲為神聖的動物,並有相關的故事或傳說流傳,但古老的信仰如今已被新的宗教觀念取代。卡達山杜順和姆律族也有捕獵穿山甲食用的習慣,但非商業用途,因此數十年前,並沒有大量捕獵的情況,對穿山甲並未構成太大的威脅。
沙巴穿山甲研究方面的先驅者艾麗莎潘姜 (Elisa Panjang)指出,如今在馬來西亞,被捕獵的穿山甲主要作為走私用途,因為價格實在太高了,人們情願出售賺錢,也不會自己吃。
在本地,穿山甲捕獵者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本地獵人或村民,另一種是設備齊全、專門進森林非法狩獵的盜獵者,他們捕獵所有野生動物,包括穿山甲。
艾麗莎表示,根據沙巴野生動物局在2018年的資料,從第一手賣給中間人的穿山甲每1公斤約240令吉,一隻成年穿山甲約4至14公斤,可想而知一隻穿山甲的收入對本地獵人或村民就很可觀了。
她指出,本地獵人或村民涉及捕獵野生動物經常牽涉社會各層面的問題如貧窮等,千絲萬縷並非那麼簡單,是否應該被責怪難以論斷,最重要的是設法阻止這種情況繼續發生。

沙恐淪走私轉運站
野外穿山甲的數量快速減少,沙巴也一樣,艾麗莎表示,如今很難看到穿山甲,如果看到可說是非常幸運的,"執法當局充公的穿山甲,比我們在野外看到的還多。"
儘管執法當局起獲來穿山甲鱗片及冷凍穿山甲相信大多來自他國,艾麗莎提醒,若沙巴成為走私轉運站,我們將失去更多穿山甲。
她指出,捕獵與走私穿山甲的情況非常嚴重,被捕獵的速快已是不正常的狀態,對比雌穿山甲一年只生一胎,根本無法填補野外大量流失的數量,專家相信若不對此採取行動,穿山甲在10年內將在野外滅絕。
穿山甲已在沙巴1997年野生動物法令第41(1)下列為一級受保護動物後,任何人捕捉、獵殺或販賣穿山甲或其肢體皆是違法,一旦被控罪成,將可被判監禁1至5年或罰款5萬至25萬令吉,或兩者兼施。
之前,穿山甲是二級受保護動物,獲得沙巴野生動物局發出準證的狩獵者仍可捕獵二級受保護動物。但該局曾強調從未曾發出任何狩獵穿山甲的準證或執照。
儘管有認為沒有良好執法,再好的法律也是枉然,艾麗莎表示,把穿山甲從原本的二級保護提升至一級後,違法者將面對更重的刑罰包括監禁,這有利於檢控,也有阻嚇作用。
她表示,世界到底還有多少野外穿山甲,不只馬來西亞不知道,全球也一樣是個謎,至今沒有適當的科學方法可以對穿山甲進行長期觀察,因為穿山甲是很難見得到的動物,難以進行科學調查。
如今最常用的方法是隱藏相機,也進行夜間觀察,尋找穿山甲蹤跡,有時也以社會科學研究方式訪問村民,但訪問村民所得的答案經常出現不一致的情況,科學家依然在嘗試尋找適當的研究方法。
她指出,每一種穿山甲的習性會根據地域的不同而有差異,並分為地棲、樹棲及半樹棲,例如中華穿山甲傾向於在地面活動及挖掘地洞棲居,它們其中一個習性是像貓一樣挖洞大便,然後把大便埋起來,而馬來穿山甲傾向於樹棲,尤其是自然的樹洞,“根據圈養的觀察,它們不會掩埋大便,而是隨處大便。”
艾麗莎表示,馬來穿山甲的研究和資料至今依然很少,“對我們來說這個物種仍充滿神秘感。”
跨國性的走私與非法盜獵是龐大的作業,單恁野生動物局一的力量是無法對抗的,她認為,野生動物局必須與所有部門如沙巴公園、森林局及警方等展開跨部門合作,“政府最終也成立了跨部門的隊伍打擊非法盜獵,這是正確的行動。”

鱗片無營養藥用價值
事實上,已有研究報告證明穿山甲鱗片是由角質素構成,是與指甲和頭髮一樣的成份,沒有營養或藥用價值,艾麗莎認為,這些研究報告的訊息沒有廣泛傳達出去,以致人們無法擺脫根深蒂固的舊觀念, 所以醒覺教育很重要。
每年2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是"世界穿山甲日",是一項全球串聯的活動,以便向大眾宣導穿山甲,讓更多人認識穿山甲及瞭解它們的困境。
自2017年以來,艾麗莎與環保愛好者與組織、社區、學校及大學等合作,配合世界穿山甲日舉行宣導活動,活動經常延綿一整個2月,並遍佈全州各地區,包括今年在京那巴當岸及亞庇等地進行,旨在教育與提升人們對穿山甲的認識與醒覺,希望人們學會珍惜所擁有的多元生物遺產。

扯上冠病 備受關注
過去,穿山甲很少受到關注,直到因大規模獵殺至瀕危,併成為全球走私及販運最多的哺乳類動物,加上如今被懷疑是2019年新冠狀病毒(2019 n-Cov)的中間宿主,而受到關注。
雖然穿山甲基於負面的理由才引起人們的注意,艾麗莎認為,事情總是一體兩面, 像因為發生冠狀病毒病疫情(COVID-19),中國政府宣佈禁止野生動物貿易活動,雖不知道是否為長久措施,她認為是很好的第一步,並希望會是長期的決策。
此外,冠病事件也讓野生動物貿易成為受到熱門的公共議題,在民間引起廣泛的討論,包括禁止野生動物貿的討論,但因過去發生過作為病毒中間宿主的動物遭大量殺死的情況,她不希望這發生在穿山甲身上。
她表示,有關的研究仍在進行中,一切仍未有定案,人們不應恐慌,她作為一員的物種存續委員會穿山甲專門小組( 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SSC Pangolin Specialist Group)在持續監督情況,"不管未來的結果如何,人們都必須知道食用野生動物的後果。"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ADVERTISEMENT































